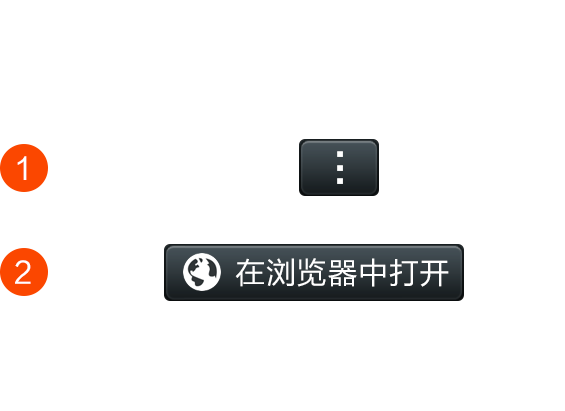“下一位。”
宁芸揉了揉眉,从随身的香囊里拿出一个小圆盒,打开盖子取一点里头晶莹的软膏抹到太阳穴周围轻轻按揉。
阿七从药材堆里抬起头来便见她不适的神情,忙上前关切道:“师姐,可是觉得累了?你连轴转了几天,不若今日就和神威堡的人道声恼,暂且歇一歇罢?”
宁芸摆摆手道:“不必,神威堡既是请了咱们天香谷来,便是对咱们的信任。况且,其他师姐妹也未有喊累要歇的,怎就我特别了?”
阿七还待再劝,帐子里的光线却是一明一暗,原是有人掀了帘子进来,便只好把嘴边的话咽下去,打量了那人一眼,转身继续捣鼓药材去了。
宁芸收回手,望向来人。他身形高壮,穿着神威弟子服很有一些英气勃勃的感觉,行动起来也虎虎生风,两三步便跨到了宁芸看诊的桌前,咧嘴朝她一笑,麦色的皮肤衬得牙口十分洁白。
“这位师兄看起来并不像抱病在身?”
“是,我没病,啊不是,我是说我要看病,但生病的不是我……”想是没料到宁芸会直接开口那样说,他回答的有些无措。
阿七闻言转身瞅着他道:“那你就把生病的人给带来!我们可忙呢,没空听你在这胡言乱语!”
“阿七!”喝止了小师妹,宁芸转头朝他歉意的笑笑:“敢问这位师兄,病人现在何处?可是不方便挪动?那我随你去看看吧……”说着就起身朝着药箱走去。
“不是不是!这位……师妹,要看病的人,现在并不在神威堡中……”或许是看阿七的脸色不好,他赶紧补上一句:“但是我能和你口述病症!我保证能说的清清楚楚!”一边说还一边拿眼去瞄阿七,这一番做派倒让阿七不好意思起来。宁芸被逗的莞尔,指了桌前的椅子道:“师兄不必着急,坐下慢慢说。”
“嗳,不瞒师妹,我是想替我娘求一个药方,她腰上不好,时常疼的不能起身……”待他口述完毕,宁芸再询问过一些细节,便已心中有谱了。那位大娘想是月子里落了些毛病,未曾好好将养,而后操心劳累,又添了些症候。
她沉吟一会写了张方子,吹干墨迹递给他,又说道:“因不曾亲眼见过病人,我便只能先给师兄列个方子试一试,若想要令堂能够痊愈,还是应该寻医当面诊治,方能对症下药。”见他面露难色,宁芸思量一遍,也晓得在这燕云大漠,寻常难有医者踏足,否则他也不必专等着天香谷来人时特特来求个方子了。再抬头看他巴巴的望着那张方子,心里头一软,开口道:“师兄若等得,待此间事了,我便与你走上一趟……”
“等得!等得!”
宁芸话未说完便被他打断,见她看过来,挠了挠头,又朝她咧着嘴笑:“我叫闫磊,师妹若是忙完了,到神威堡天刀营寻我,随便找人一问就是!那,那师妹你忙,我先走了!”
待人出了帐子,阿七按捺不住的笑出声:“师姐,他莫不是怕你反悔,才走得如此匆忙!连咱们姓甚名谁都不问,倒仿佛知道你是个言出必行的主儿呢!”
宁芸也笑,临了却摇头一叹:“神威弟子一腔为国为民之心,在这燕云坚守多年,实是辛苦!”
此后半月里,宁芸帐前三不五时便会出现一束清香的小花或是几个洗净的野果,连阿七都叹了一回:“那憨石头倒也算有心。”宁芸却笑笑道:“也未必就是他。”过得几日,不再有东西出现,阿七撇嘴道:“白夸了!”宁芸只摇头一笑便又低头整理脉案去了。
又是小半月过去,天香谷众人一直忙于为神威弟子看诊问药,直到辞行前夕却忽然传来西夏进犯的消息。领头的师姐召集师姐妹们商量后,决意留至此次战役结束再行离开。
既是要留下,宁芸想着先去与闫磊打声招呼,等此战结束,自会去为其母诊治,便一路寻到了天刀营中。
“你找闫磊?”
“正是,不知师兄可知他此刻在何处?”
被宁芸询问的神威弟子张了张嘴,最后只是干脆转身道:“这位师妹,随我来吧。”
再见闫磊宁芸皱起了眉,他瘦了些,想是连日操练的原因,整个人的精神也有些萎靡。看见她的一瞬间眼神波动,开口声音喑哑:“师妹,你来啦。”
宁芸不喜闫磊如今这副好似不堪受训的模样,简短向他说明来意后便出言告辞。念他一片孝心赤诚,临走从药箱里摸出几个常备药包递过去:“这里头有提神的,有治外伤的,用途都写在药包外面了,开战在即,师兄也要保重自己。”见他仍有些怔愣,把药包往他手里一塞便出了门。
先前送宁芸过来的神威弟子见她出来,复又上来给她引路,几番踟蹰,行至半道才问她:“师妹,闫磊的情状看着还好?”
宁芸还记得这人先前的欲言又止,见他这样,蹙眉问道:“可是出了什么事?”
那引路的弟子微叹了口气:“前几日接到消息,他母亲去了。”
宁芸顿住了脚,想起才刚与闫磊说的话,饶是再不想迁怒旁人也不由恼道:“师兄怎不早与我说!”
宁芸到底未再去寻闫磊,他俩结识的原因便是那一张再也无法发挥作用的药方,已经在不经意间往他伤口洒了把盐,再特意出现在他面前无疑是又一次的戳痛他。况且连日来众人的心弦都因为临近开战而紧绷着,宁芸也实在是没有那个精力在此时去纠结这件事。
转眼战争便拉开了序幕,对于神威弟子来说,这不过是他们所经历的其中一场。而对留下来的天香弟子们来说,这将是她们一生都难以忘却的场景。
与任何的江湖械斗都不一样,低沉的战鼓似擂在人心上,千万人的喊杀声交织在一起,战马的嘶鸣,刀枪的碰撞……殷红的热血成了这戈壁大漠唯一的艳色。
即便只是守在后方照顾不断添加的伤患,天香诸人也能想象到战场上的厮杀有多么惨烈。
心里存了愧疚,宁芸便有些在意,既不希望看到闫磊在伤患里出现,又害怕他到最后也没有出现。
再听到闫磊的消息,是从那个曾为她引路的师兄口中:“那小子不要命了!”
也许是一时冲动,也许是生平第一次直面战争的刺激,宁芸仅凭着这一句不清不楚的话便提了伞中剑冲进了千军万马中。
在人群中准确找到一人的机会有多渺茫?更何况是这样兵荒马乱的时候。宁芸反射性的躲避,格挡,回手反击。眼前早已看不清任何面孔,虎口崩裂沁出了血珠,耳中嗡嗡作响再听不明声音,气力快要用尽,脑海里闫磊的脸却越发清晰,找到他成了她撑下去的最后一个信念。
感受到背后有人靠近,宁芸不及回头便劈出一剑,却在余光瞥见的己方服色下生生转开了手。未尽的动作将她带了个趔趄,随后被谁扑了满怀,耳边嘈杂褪去,有人轻声道:“好歹这一次赶上了……”
之后是如何被赶到的师姐所救,又是如何被带回了营地宁芸已经完全没有了印象。她的记忆里最鲜明的是怀中人胸口上突兀的半截箭头,是无论如何也止不住的血,是不论怎么抱紧都还是渐渐冷却下来的体温,以及那些断断续续的语句:“你的眼睛真亮……能不能用这双眼……替我和我娘……去看看战场外的……那个江湖……”
闫磊说这话的时候努力朝她抬起手,好像是想抚一抚她的眼。宁芸伸手去握,那只大掌却在半途颓然坠落,手腕重重砸到她的面前。她几乎是茫然的看向他紧闭的眼,半晌才带着木然的表情将脸缓缓埋到他掌心。在一片黑暗中,她终于低吼着呜咽出声,滚烫的泪从他指缝间跌落,刹那间失了温度。
天香谷的宁静祥和并不因时光的流逝而更改,终年草木繁茂,花海飘香,似乎所有的纷扰都被挡在了外头,一丝也浸染不到其中。
阿七从信使手中接过画卷,道了声谢便朝着青囊阁方向走去。行至半道就被师妹们拦了路,围着她叽叽喳喳的嚷开了。
“阿七师姐,宁师姐的新作拓本到了吧?让我们先看看嘛!”
“阿七师姐阿七师姐,上一次宁师姐的墨宝录画的是秦川吧?这回还是在那边吗?”
“阿七师姐,这都走了好一阵子啦,你累不累?我帮你抱画啊!”
“阿七师姐……”
实在拗不过这群小丫头,阿七抽出画卷在道旁的凉亭桌上铺将开来,嘴角的弧度却凝在看清画中之物的那一瞬。
眼看阿七脸色不好,几个小姑娘也安静下来,你推我我搡你,最后年幼的小师妹揪住阿七的衣角,让她回了神。
阿七同她们笑笑没说话,只把桌前的位置让给小姑娘们,她则退远了些,片刻后转身步出凉亭,仍旧拾阶而上。
身后叽喳的讨论声顺着风断续传来,那一幅描绘沙场的画卷显然足够她们惊叹许久。
如果不是这幅画,阿七自己都不会意识到那一片大漠究竟给她留下了怎样深刻的记忆。她突然觉得这些年都误会了宁芸,她一心游历并非所谓为情所哀。作为距离最近的旁观者,细究下来,阿七发现那二人之间竟真的算不上有什么深厚情谊。可就是这样的两个人,一个于千军万马中为对方挡箭而亡,另一个独自踏过万水千山只为了兑现那句“替我看江湖”。
这是情?
抑或不是情?
或许,已经不重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