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文化的精髓在于延伸和拓展,克苏鲁也不例外。
克总发糖、SAN值归零,如果你在B站看过的视频够多,那或许对上述两个名词多少有点印象。
1920年,克苏鲁神话的奠基人洛夫克拉夫特在一次诡异的梦境后写下了第一位克苏鲁外神“奈亚拉托提普”的名字;100年过去了,四处飘荡的邪神意志不仅没有随时间消解,反而在小众圈层里悄然“支配”起了一批“狂热信徒”,固执地霸占起网络空间里的小小一角。

阿撒托斯、犹格·索托斯,莎布·尼古拉斯、克苏鲁……一个个邪恶的名讳拧动着时空之钥,挣扎着要脱出百年囚笼,想要在当代文化史上留下一笔,却绝望地发现无论它们如何有心,却怎么也使不上劲儿。
就算在它本应最擅长的游戏、影视领域也是如此。细致入微的设定和引人入胜的氛围似乎对如何构建一个足够有吸引力的恐怖世界束手无策。克苏鲁神话,这个在ACGN圈如雷贯耳的名号,最终仅困在一个特定的亚文化圈里,是时代变了,还是克苏鲁自己的问题?
 洛夫克拉夫特(Lovecraft,昵称“爱手艺”)
洛夫克拉夫特(Lovecraft,昵称“爱手艺”)到底什么是洛氏恐怖?
在开始这段昏暗混沌的旅程前,让我们先试着用洛夫克拉夫特最喜欢的句式造个句吧:“惨白险恶的月亮可憎地悬于空中,将我的身影扭曲成无可名状的混沌,我不安的灵魂也疯狂地暴露在灼灼月光下。”
怎样,有克苏鲁的那股味道没?即便你从未读过洛夫克拉夫特的着作,你对他的写作风格应该也有个模糊的印象了:黏糊,就像克苏鲁神话中的经典符号触手一样。

“可憎”、“险恶”、“无可名状”、“不可描述”都是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高频词汇,他习惯用语焉不详、欲言又止的语句来描绘想象中的邪神、宇宙、本源以及混沌。
比如在洛夫克拉夫特的经典作品《疯狂山脉》里,他曾长篇累牍地以科考日志的形式描述群山、失落的城市,乃至每一处环境细节,希望借此营造恐怖氛围,暗示邪恶的生物便藏身其中;再比如在《黑暗中的低语》中,他又不厌其烦地用一篇篇书信,逐渐将读者拉进佛蒙特山间的乡野异闻,最后再揭开恐怖事件的神秘面纱。

总之,洛夫克拉夫特非常执着于用云遮雾绕、闪烁其词的叙述一点点拨开迷雾,然后将恐惧呈现在读者面前。
可惜在当时洛夫克拉夫特的理念并不被世人所理解,在世时,他写的数十部小说市场反应寥寥,直到他凄然离世后,洛氏恐怖才广受追捧,为其博得古典恐怖小说大师的称号,此后更有无数创作者在此体系上不断添砖加瓦,并最终诞生了名曰“克苏鲁”的一整套神话体系。
然而,真正让洛夫克拉夫特始料未及的是,克苏鲁神话在其他载体上极有可能散发出较文字更为耀眼的光芒。
 《血源Z咒》的世界观借鉴自克苏鲁神话
《血源Z咒》的世界观借鉴自克苏鲁神话优秀的克苏鲁游戏在哪里?
活跃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只顾埋头笔耕的洛夫克拉夫特不可能想到,百年后,富媒体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会远超文字,而恐怖题材的内容通过声音、画面放大后会有这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加上了交互属性的游戏会令玩家如此欲罢不能。
随着游戏开发技术水平日益提升,恐怖类游戏如今已成为当代游戏门类中的重要题材,《逃生》《黎明杀机》《零》是玩家口中言必称之的佳作,由经典IP“生化危机”、“寂静岭”改编的电影成功出圈,前者更凭借过硬的重制版品质持续圈粉、圈钱。
 《生化危机3重制版》快要上线了
《生化危机3重制版》快要上线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既然恐怖题材这么热闹,那优秀的克苏鲁题材游戏又在哪里?
2018年,《克苏鲁的呼唤(Call of Cthulhu)》“隆重”上线,与洛夫克拉夫特经典小说同名使得它备受洛氏拥趸期待。
 克苏鲁神话真的就是由这些黏糊糊的血肉组成的吗?
克苏鲁神话真的就是由这些黏糊糊的血肉组成的吗?但等到游戏上手,玩家才发现味道根本不对,他们想要的是层层剥落疑点,接近真相和疯狂的快感,体会无法理解的未知恐惧,而非挂着“克苏鲁”、“死灵之书”的表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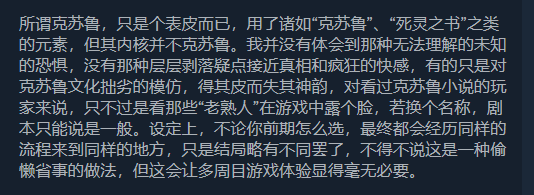
2019年10月,挪威独立游戏工作室Rock Pocket Games推出了一款以太空基地为背景的克苏鲁恐怖游戏《疯狂之月(Moons of Madness)》。

按理说,将故事舞台搬到外太空的《疯狂之月》本可以将深空恐怖发挥得更好——毕竟克鲁苏神话里所有的生物都来自地球外,可是除了jump scare演出和恐怖游戏的必须要素音乐外,玩家几乎找不到太多共鸣,部分玩家甚至认为游戏性缺失导致它更像一款步行器模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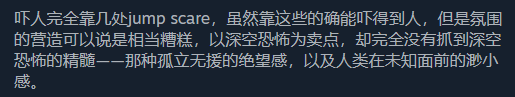

同年早些时候上线的还有Frogwares打造的《沉没之城(The Sinking City)》,玩家需要扮演一名侦探探查神秘受灾的城市。

曾开发过《福尔摩斯》系列的Frogwares显然更懂得如何用画面、音乐等气氛烘托绝望氛围,但他们还是不小心触碰了克苏鲁神话最不该被触及的红线——倘若玩家可以用手枪击退步步紧逼的丑恶怪物,那还有多少克苏鲁味道可言呢,它与一般的恐怖游戏有何差别?
 要知道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角色大多时候是没有勇气面对异形怪物的
要知道洛夫克拉夫特笔下的角色大多时候是没有勇气面对异形怪物的截然不同的游戏设计,两相背离的玩家建议暴露了克鲁苏题材作品中最大的矛盾——一边是克苏鲁玩家需要在游戏里追求游戏性和未知体验,一边是被画面、动作、音乐、声效巨细靡遗地具象化后的怪物要如何重新降维到“未知”。
与此同时,经历了几款克苏鲁游戏“教育”的玩家还揭露了制作该题材内容时最核心的难题——“克苏鲁悖论”:如果读者、观众或玩家在观看或打开克鲁苏电影、游戏前就知道它是克苏鲁题材,那它就一点都不“克苏鲁”了,所谓“对未知的恐惧”这时已然荡然无存。
绝大多数克苏鲁题材的游戏惨遭滑铁卢,也让我们不禁沉思,克苏鲁真的适合装在游戏或影视的瓶子里吗?我们在恐惧未知的时候是在害怕些什么?
克鲁苏真的有那么恐怖吗?
如果撕开克苏鲁神话的外皮,将洛氏世界观放在放大镜下细细观察你会发现,所谓的“神话”其实彻头彻尾都是科幻小说故事,而洛氏恐怖也不过他对无限深空的幽暗迷思罢了。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科幻小说正处于由萌芽初创时代(以凡尔纳、威尔斯为代表)向黄金时代(以科幻三巨头为代表)转变的过渡期,科幻小说家们对太阳系充满遐思,幻想了无数太空歌剧式的科幻故事,星际飞船穿梭其间,太阳系帝国兴起又衰亡。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之《海底两万里》
凡尔纳科幻三部曲之《海底两万里》也正是那个时候,1930年,太阳系第九大行星冥王星(虽然早已被开除出行星行列)被人发现了,此时距离伽利略第一次观测到海王星已经过去了足足三百多年。对此人们惊愕万分:太阳系的边缘尚且如此遥远,那实在无法想象在浩渺的星海深处还有哪些未知在等待探索。人类是多么渺小!
身处那个时代的洛夫克拉夫特自然逃不出历史局限性,只是他的看法要比当时主流的浪漫主义宇宙观深邃、阴暗得多。事实上,在洛夫克拉夫特书中,他不止一次地用“像冥王星一样遥远”、“比冥王星还遥远”“来自太阳系边缘的星球”一类的词来形容造访地球的邪恶生物来自于多么遥远的星空,这些生物又是如何与地球生灵不同。
 曾几何时,冥王星就是我们想象的边界
曾几何时,冥王星就是我们想象的边界他在《黑暗中的低语》里写道,外形介于昆虫和真菌之间的“米·戈”挥着翅膀在星际以太(Ether,五大元素之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存乎于天空之上的物质)中飞行,为采集矿石在地球建立据点;此外还有先进的科学技术,能够进行大脑移植手术。

《疯狂山脉》里的神秘生物“古老者”外形酷似植物,身躯如纺锤状大桶,长着海星状的五条扁平长臂,曾经在南极建立起迷宫般的巨大城市,拥有发达的雕刻及壁画艺术。

《穿越时间之影》所记述的“伊斯之伟大种族”的科技则更加奇奥,它们可以将意识投射到任意一个时代的种族身上(简而言之就是时空穿梭和肉体夺舍),以此观察和记录每个种族的社会、生活、科技,俨然扮演起宇宙史官的角色。

好了,到这里有些人会觉得,洛夫克拉夫特絮絮叨叨半天,结果讲的还是外星人入侵地球的故事嘛,用网友的话说,你克总再怎么牛掰也就是个“星际交换生”的角色。
而这些对当代人来说太司空见惯了,我们被充斥着外星人元素的科幻影片洗礼太多遍了,再恐怖撑死也就《异形》《普罗米修斯》《异星觉醒》的水平了吧,大不了一死,如此看来克苏鲁也没什么了不起。

这当然不可能是克苏鲁的全部——克苏鲁从来不是一本打开供人解读的书,而是从纸缝里对人性深渊的疯狂窥视。
克苏鲁的核心究竟该怎么诠释?
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维特根斯坦曾在其撰写的《逻辑哲学论》里说: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
这句话放在洛夫克拉夫特身上大概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书里俯首即是诸如“不敢想象”、“不敢说出”、“超越智识”的字眼,煞有介事地描写人类在瞥见宇宙尽头的真相后陷入谵妄、疯狂,却始终掩盖不了文字表述上的苍白、乏力、困顿及无奈。

语言像一道栅栏,把洛夫克拉夫特式的“对未知的恐惧”牢牢困在原地,毫无信马由缰的空间;但语言又似一把梯子,也许只有靠着攀爬它那颤颤巍巍的阶梯,人类才有幸一窥“未知恐惧”的全貌,而在游戏范畴内能将其做到极致的似乎只有文字AVG。
作为日薄西山的游戏品类,文字AVG没必要也不值得被神话,但匪夷所思的是,在悬疑、猎奇、恐怖等题材的加持下,它又拥有某些奇妙的魅力。究其原因,大抵是抽丝剥茧的文字叙述和无可挽回的线性剧情(顶多给你几个选项)会将玩家一步步推向血淋淋的真相,结局不能拒绝,无法逃脱,不可撤销。
比如玩家只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就可以玩完/看完虚渊玄的《沙耶之歌》,但就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玩家可以扮演一名感知失常的男人,体验一个病态世界,与一个谜之美少女陷入绝望凄美的爱恋,最后一路奔向令人心悸的终末。
 Steam售价69元,游戏时长极短,94%的好评率,这绝不是情怀那么简单
Steam售价69元,游戏时长极短,94%的好评率,这绝不是情怀那么简单更微妙的是,搭配上BGM的视觉小说突然有了不一样的感官冲击力——它好像介于多维的角色扮演游戏、电影和一维的书籍之间,更容易予人以沉浸感和真实性;而BGM则犹如一枚恰到好处的拨片,不留情面地,催人发疯地刮弄着玩家大脑里最脆弱的那根神经。
到这里,我想克苏鲁核心该如何诠释的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语言的边界是小说和文字AVG最大的不幸,却又是最大的幸运。语言给它们套上了枷锁,但也留下了足够的空白和未知,未知即是克苏鲁最晦暗、最迷人之处。
克苏鲁神话的终点在哪里?
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而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是对未知的恐惧。
这是克苏鲁信徒们提到洛氏恐怖时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但无论是克苏鲁创作者还是受众似乎都没有完全吃透它(也许洛夫克拉夫特本人都没做到)。因为当你刻意要将作品照着克鲁苏模子来创作或理解的时候,你就输了——实际上,大部分影视、游戏作品都无法脱此窠臼。
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电影《灯塔》的导演罗伯特·艾格斯则要高明得多,面对记者发问,他坦言喜欢洛夫克拉夫特对“恐惧”的内在意义的挖掘,但从来不承认克苏鲁神话左右过电影创作;可另一方面,在《灯塔》里,触手、人鱼、迷雾等意象又若有若无地向观众呈现着经典的克式惊悚符号。

最妙的还要数电影最后,男主不惜杀死守塔人只为登上灯塔看看那里究竟有什么,却在目睹真相后瞪圆双眼,歇斯底里地哀嚎、尖叫,跌落塔底。至于他在灯塔上到底看到了什么,电影绝不会傻乎乎地告诉你。

显然,导演罗伯特·艾格斯当初的回答不够老实——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留白更克苏鲁的处理方式了。男主比谁都清楚灯塔上等待他的只有悲剧的宿命,但他还是不受控制、不自觉地一点点接近命运的终点,直至窥见真相丧失理智。这不正是洛氏恐怖的精髓,“不可名状的恐惧”吗?
相似的还有《美好的每一天(素晴らしき日々 ~不连続存在~)》,当玩家自以为读懂了游戏的全部,却在抵达真结局时愕然发现所有剧中人的命运都摆弄在外神犹格·索托斯的掌心里。他嗤笑着欣赏人间闹剧,恣意品玩世人知晓真相后步入癫狂的姿态。
 门之键(门之钥),亦即犹格·索托斯,克苏鲁神话中全知全视的存在
门之键(门之钥),亦即犹格·索托斯,克苏鲁神话中全知全视的存在克苏鲁的未来归于何处?
在克鲁苏神话诞生整整100年的当下,“行文拖沓,节奏缓慢,故弄玄虚”,逐渐成为许多读者对《克苏鲁神话》原着的主流看法,快节奏的生活叫人们无法忍受那些冗长唠叨的心理独白和大段大段的景物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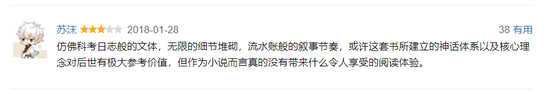

尽管它的信徒依然活跃,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克苏鲁注定是小众圈层内的狂欢,它不会因为某个特定文化符号出圈(比如文章开头的“SAN值归零”)变得流行。而作为其追随者,他们唯一能做的是把克苏鲁神话中的诸多元素揉碎了融入大众题材作品里,使之更易被接受、消化。
 《魔兽世界》里的上古之神就借鉴了克苏鲁神话,在这之上还衍生出了虚空大君的设定
《魔兽世界》里的上古之神就借鉴了克苏鲁神话,在这之上还衍生出了虚空大君的设定就如克苏鲁神话里的那些天外来客一样,虽然它们是异乡人,但来到地球后,还是会主动乔装潜藏,乃至最终演变为地球的主人。
来源:游戏陀螺






